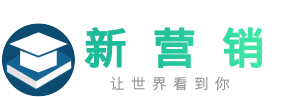善后、救济和难民问题:一位作家的经历和反思
1979年10月,英国著名小说家和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应邀随英国作家代表团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在她之后写的日记和书信中,食物、居所等字样屡屡出现。她在致友人斯科特·邓巴的信中写到,这里“所有的人都食可果腹、衣可蔽体、居有其屋”;在致密友、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1920-2010)的信中说,她注意到这里“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也没有饥饿!没有人躺在大街上。”这样的书写一方面表明在赴中国访问之前默多克的认识中可能存在的预设,另一方面也说明食物、居所是她的一个重要衡量尺度。毋庸置疑,这与她在二战后的一段特殊人生经历有关。1944至1946年,她在英国、比利时和奥地利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政官员,其中前十五个月在总署的伦敦办公室从事善后工作,后十个月在欧洲的难民营为因战争而失去家园者从事救济工作。相对于关于战争和战后重建的宏大叙述,默多克留下了一位正处于成长期的女作家视角独特的敏锐观察和深度思考,对难民问题的反思以及苦难对人性产生的影响日后成为其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青年艾丽丝
善后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联合国难民署的前身)成立于1943年。这是第一家以联合国名义运行的机构,根据一份英国皇家出版局1944年出版并分发给所有英国重要新闻机构的小册子,“在由联合国武装力量解放的地区,或者敌人撤退后的地区,所有人口都将立刻获得援助和救济、食物、衣服和住所,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他们当中苦难最深重者,莫过于八百多万难民(一年之后这个数字大幅上升)。在这群因战争而丧失家园、陷入绝望的人当中,默多克注意到,有许多人被他人当作“动物或奴隶”来对待。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联合国难民署的前身)
1944年6月,默多克申请并加入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她想在“救济”方面做一些工作。整个战争期间她都对那些离开英国参战的人“怀有一种野蛮的妒忌”,多次抱怨“我关于生活的知识绝大部分都是二手货,对此感到十分痛苦”。她在申请表里写下了自己的心愿:她希望“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在书桌前,希望尽可能离现场近一些”。事与愿违,她获得了“善后”而非“救济”方面的工作。在她看来,这意味着她将继续留在伦敦,被毫无意义的事情所折磨:“关于‘善后’谁会去听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后来的事实确证了她的预感。她决定通过“拉关系的可耻手段”奔赴“现场”,然而她的计划落空了,她在总署设在伦敦的地区办公室“蹉跎”了十五个月。
尽管默多克日后在多次访谈中把在总署的两年说成是“我做过的最精彩的事情之一”,但是伦敦岁月的见闻令她倍感受挫。在总署办公室的经历让她直观地感觉到美国与英国、欧洲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她在1945年7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不是由伊林和达根汉姆的圆顶礼帽管理的,他们至少行为举止接近绅士,而是由康涅狄格州密尔沃基、辛辛那提和纽黑文的市民,这些人要尽其所能给摇摇欲坠的欧洲致命的一击。在无数书桌后面,他们不是坐在而是懒洋洋地斜靠在办公凳上,束着纤维皮带和尼龙背带,嚼着口香糖,用教名称呼同伴……
亨利·詹姆斯笔下美洲新大陆与欧洲旧大陆之间的著名对比,在这里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老欧洲的绅士与新大陆的牛仔。默多克采用一种提喻法(一种用局部代表整体或用整体代表局部的修辞手法),呈现出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那群从新大陆远道而来的人不仅与“伊林和达根汉姆的圆顶礼帽”所指代的英国人形成对照,而且毫不留情地要给欧洲“致命的一击”。
默多克一边把办公室当作逢场作戏的地方,一边冷眼旁观。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在总署里一种丛林生活盛行起来,“到处都是笨拙的英国公务员(……比如说,我就是)和野心勃勃的美国人及加拿大人……很多拥有高贵心灵、满怀良好愿望的人被淹没在平庸和混乱的洪流中”。在她工作的前几个月,这个机构几乎无法正常运行。半年之后,它就像“一场疯狂的表演,里面都是特别出色的人,但他们没有集体荣誉感,对如何让一个行政机构运行下去毫无概念”。一年之后,她依然觉得“一如既往,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里一片混乱……目前,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向流离失所者运送物质”。到1945年6月,总署的轮子才终于全速运转起来了。
从默多克的“善后”工作经历中,我们能清晰看出的,不是她真正为难民做了些什么,而是她对美国与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权力对比的敏锐感知。办公室的丛林法则向她表明,人在自然状态下一般不会与他人建立起兄弟情谊。尽管如此,她有时能看到她所做的事与某些人是否有衣蔽体、有食果腹、心灵是否得到抚慰有一种远程联系。她渴望近距离接触难民,从事她所希望的“救济”工作。 1945年8月,她终于被派往欧洲十个月。
救济
默多克在比利时停留一段时间之后被依次派往奥地利的四个不同地区从事救济工作,亲眼见证了一个“完全崩溃的社会”。1945年12月中旬,她首先被派驻奥地利法语区总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这里依旧远离难民营,她的工作涉及营地的建设和资助、与政府部门签订互惠合约。当地几乎没有商店,食物极度匮乏,交通线路被严重损毁。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人们必须以物易物,香烟成了硬通货。令默多克痛心的是,生活物资上的异常艰苦对人性造成了伤害和摧残。她在信中写道,她打交道的是“敏感的法国人和闷闷不乐但彬彬有礼的奥地利人,还有成千上万悲惨的流离失所者,他们被集中到位于意大利和瑞士之间的这一小块地方。在经历过诸多适者生存的训练后,如今许多人都已经变成了坏蛋,让人对他们不知所措”。对于苦难导致的结果,她愤怒而沮丧地感叹,“在这场战争中,有多少生命被不可挽回地摧毁了……在这些人的前方,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为了生存,他们别无选择:“流离失所者要么冷漠,要么会成为暴徒或骗子。”在日后四十余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默多克从未歌颂过苦难及其所谓的净化功能,而是揭示出对古希腊人来说如此真实的“埃特”(Até)思想,即苦难从一个人近乎自动地向另一个人转移。
默多克被派往的第二个地点是普赫(Puch)。这里有一个大营地,秩序混乱不堪。她的工作包括辨别新来者的身份,找出他们有何种一技之长,想去哪儿,并为他们安排住宿,获取毛毯等。这里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仍是食物问题。本来对于很多奥地利人来说,从德意志帝国的铁蹄下获得解放,只不过意味着定量口粮下降到维持生存所需的水平。在总署援助的国家中,奥地利的定量口粮最低,维也纳最主要的食物是面包和土豆,死于肺结核的人越来越多,市长面临暴乱的威胁。与奥地利人相比,流离失所者的情况更糟糕。1946年3月,普赫出现了令人恐慌的食物短缺,总署不得不在意大利四处搜刮,甚至沦落到“购买法国骑兵的老马”为食的地步。为了能够搞到食物,默多克和同事们用上了各种“狡猾、大胆和机会主义”的办法,她还派过马车去英国军营乞讨剩余食物。
在极端困境中,人性的诸多面向得以暴露。默多克观察到,这里有一个“如地狱一般腐败的”天价黑市,主要由南斯拉夫人操纵,几个总署新职员卷入其中,一磅黄油卖到二点一英镑,五十公斤可以换一件上好的皮衣。红十字会的包裹常被快速转手,用来交换各类物品。此外,她还发现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多,营地逐渐变得拥挤不堪,来自不同民族的人普遍表现出痛苦而愤怒,时常相互敌对仇恨,打架斗殴的现象频频发生。老年人是最绝望的一个群体,最可怕的悲剧通常发生在他们身上,因为“再也没有人需要他们了”。有技能的年轻人或许还能幻想未来有一天他们会建立新家园,融入新国家,他们靠着这种希望坚强地活着。
3月下旬,默多克被派往第三个地点克拉根福(Klagenfurt)。她在途经维也纳时显然体验到了英国官员的另一种生活,在信中兴奋地告诉友人,她在金碧辉煌的金斯基宫跳了一个晚上的舞,“那里现在是英国官员俱乐部……总司令部在美泉宫!宫殿上下直至枝形吊灯上最后一座闪闪发光的尖顶,全都完好无损”。室内的富丽堂皇越发映衬出室外的满目疮痍:昔日繁华时尚的克恩顿大街如今被瓦砾碎石所阻断,上面赫然停着一辆烧焦的坦克的躯壳。她在致菲利帕·福特的信中写道,“每一条大街小巷上,砖石堆积如山,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所有的废墟金光闪闪。歌剧院成了一个华丽的贝壳,教堂失去了屋顶,被轰炸得千疮百孔,但华美依旧。”在维也纳短暂停留后,默多克来到克拉根福,在奥地利英国区总部工作,住在城外十公里处精致的沃瑟湖畔,它“湛蓝、静谧,被群山和森林环绕,古堡倒映其间,一切都显得那么珍贵,我久久凝视它,一直惊叹不已”。无论处境如何,默多克终其一生都能够对世界上不可思议的美有所察觉,这正是她的力量之所在。她的工作“一如既往,徒劳无益,我比在因斯布鲁克时更与世隔绝了,远离营地和无家可归者,真遗憾”。
大约是从1946年4月下旬到6月下旬,默多克被派往了最后一个驻地:霍奇施泰因加塞(Hochsteingasse)的一个前线营地格拉兹(Graz)。这里曾经是一个希特勒青年营地,1946年2月被改制成宿舍,供流离失所者中那些历经重重障碍,最终被格拉兹大学录取的学生居住。当时有来自十二个族群的二百零八名学生,斯洛文尼亚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克罗地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尽管民族各异,但是共同组建了一支足球队,默多克从中看到了希望的微光。此外,这里还有八个“无国籍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灵魂,没有家园的灵魂”。默多克称他们为凄惨的无辜受难者,因为没有国籍成为了他们的“罪”,她日后写道,“在一个没有身份就是犯了滔天大罪的世界上……此罪大过任何其他的罪。此罪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处罚。”
1946年7月1日,默多克正式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辞职,途经巴黎回到英国。她为难民工作的经历虽然短暂,却为她的人生和创作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难民问题
难民在默多克的想象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她认为流离失所既是政治状态,也是精神状态。她赞同神秘主义哲学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相信真实的社会充斥着政治、军事、社会、文化、金融等各种权力,权力的滥用势必导致苦难和受难者,最典型的莫过于二战中突然失去家园、家人、身份、自尊和食物的难民,而世界上所能存在的最可怕的剥夺就是摧毁一个人的过去和文化。默多克持续思考丧失家园造成的影响,并在小说中对此加以艺术化演绎。
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
在默多克的多数作品中至少有一位难民,他们的共同点是因某种非他们所能掌控的权力而被剥夺了在一种文化和国家中原有的家园。这种剥夺给他们带来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再也无法与他人建立起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他们未必如很多人相信的那样会因失去家园、历经苦难而变得高贵。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在现实中苦难是使他们陷入困境的一种形式,必将导致更多的恶。恶在这个世界上以受难的形式蔓延滋长,导致他人受难是恶的受难者化解自身苦难的一种最简便方式。如果被剥夺者没有堕入倦怠状态,他们就会去伤害和剥夺他人的家园。由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世界永无宁日。
不仅如此,在默多克的小说世界里,除了战争导致的难民之外,还有更多广义的难民。1957年有人批评她在最早出版的两部小说中刻画了格格不入的人、古怪的人、流离失所者等,他们都带有某种难民的味道。她对此回应道,现代西方人在他们的社会和世界里并不感到舒适自在,“我们并不像我们的祖父们那样在社会中感到很舒服。社会本身变得问题重重,不可信赖。因此,难民这个真正意义上的丧失家园者,似乎成为当今时代人的恰当象征。”1982年默多克再次就其小说中的难民评论道,“这是人类苦难的形象,是我们遇见的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是一扇扇窗户,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看见可怕的世界。”
对于如何挽救这个“可怕的世界”,让流离失所的难民重回家园,默多克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不过,在上下求索时,她时常将目光投向东方,在她的多部作品中——如《逃离巫师》、《好与善》、《海、海》等——都有一位来自西方的寻觅者在古老的东方文明中流连忘返。或许,作者本人从中看到了希望。
本文由本站作者发布,不代表新营销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www.newmarketingcn.com/xinzhishi/428619.html